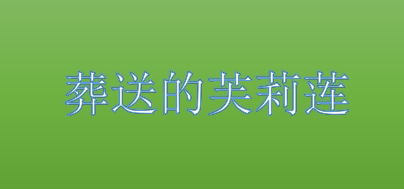北京晚报 | 作者 胡月
《城史记:我读过的十座城市》《说史记:小说一样的历史》《野史记:近代中国异闻录》 杨早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 (相关资料图)
(相关资料图)
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是准确的吗?或许我们能说出历史事件、时间及意义,但历史总有复杂的一面,那些历史中明线往往为人们所知被人们翻来覆去地分析,但那些历史的暗线藏在明线之下,或许对历史产生不了多大的影响,但却大幅提升了历史的魅力。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早,以《城史记:我读过的十座城市》《说史记:小说一样的历史》《野史记:近代中国异闻录》三本小书,展开“杨早讲史”系列丛书的序幕。通过个人随笔、小说化历史、历史掌故这三个方面,讲述他与历史与文学的不解之缘,品读历史的乐趣。
《城史记》以富顺、成都、广州、北京、天津、高邮、南京、上海、西安、合肥这十座与作者成长生活密切相关的城市为主角,在记录这些城市另一面时,将个人与历史连接起来,从城市文化中看见自己,从自己的经历中看见城市,似乎在写一部很新的自传。《说史记》与《野史记》则抹去了个人,更添了一份历史的严肃感,但在作者以小说写史,以掌故读史的基调下,这份严肃感并没有多厚重,而是显得轻松活泼。
作者摘取历史大人物大事件的边角料,聚焦在清末民初这段历史节点上,讲述了清末民初大臣们的八卦、“五四运动”历史背后的细节、民国时期大学教授的逸事趣闻和近代新闻业的血泪往事,既有直击现场的历史还原,也有犀利尖锐的人物评论。在小说、小掌故的辅助下重述故事,其意并非在于要以大发现改变些什么,而是以细碎、复杂的故事重现鲜活的历史场景,让读者充分体验历史的复杂性和通过文字阅读带来的现场感。
老北京的变迁
《城史记》中北京作为作者现在生活的城市,他在讲述北京的开篇就写道: “我在北京已经住了廿四年,它是我一辈子住得时间最长的地方。”
作者在书中提到,北京最难以抹去的符号就是首都,在历史资料中,清末民初的北京大街,可以并行十辆车,这是何等宽阔。后来1928年民国政府定都南京,北京便改名北平,列为直辖的“特别市”,而后再降为隶属河北的普通市。于是官宦、商人纷纷迁移,房价大跌,市井萧条,基本上只剩遗留在北京的各种大学和文化机构,变成了学生城市。
当时的北京有那么几条街是非常聚人的。当时的文化人最偏爱琉璃厂,学者们在琉璃厂聚会,或者是相约或者是偶遇,彼此间见面的机会远超其他场合。而琉璃厂之所以有这样的相遇,全仰赖于它是当时北京规模最大的旧书市场。
琉璃厂的文化气息源自乾隆年间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,全国的图书都涌向了北京涌向了琉璃厂。旧书古籍在这里经久不衰,以至于清末上海的新式出版物来到北京琉璃厂,都要被挤对讥笑一番,这也逐渐塑造出琉璃厂的风格特色,新文化人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,因研究所需,需要占有大量资料。这时琉璃厂的旧书肆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,店员素质之高,找书能力之强,服务热情态度周到,能和这些大教授谈天说地,这就使得琉璃厂与近代学术史关系密切。以鲁迅为例,他1912年来京至1926年南下,十五年间,去琉璃厂的次数达四百八十五次,采买图书、碑帖三千八百多册。
随着新式出版物的蓬勃发展,琉璃厂的旧书肆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,书中提到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文学作家,笔触很少提到琉璃厂书肆,即使偶尔提到,也只是将琉璃厂看作传统文化一道残留的风景线。北京的文化与商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,在北京,诸如琉璃厂这样的文化商区与现代学者关系至深,但人们却很少提起。或许在北京,文化场所就如同空气一样,随处可见,早已形成氛围,无需再将符号一遍遍提起。
对于当下在现代都市北京生活的年轻人们来说, 少有人仍旧过着老舍话剧中的老北京生活。每个人对于北京都有不同的感受,这也创造出多样的归属感。
大师们的小故事
《说史记》和《野史记》中讲述的主要是清末民初这段时间的各种大小事,有说人物的,有说事件的,有说报纸杂文的,有对历史的再评论,总之突出了这段历史时期的广度。《野史记》中“大学,有大师之谓也”这一章,通过文人大师之间的趣闻轶事,讲述在严肃百科之外的他们——比如闻一多和朱自清。
闻一多其人才华横溢,有着诗人奔放的热心,而朱自清则相反,他内敛低调,内心常有文人的忧愁与焦虑,相比较闻一多他的内心活动更加丰富。从他们演讲和讲课中就能看出一二,在作者《大师不会讲课,又怎样》这篇文章中,朱自清与俞平伯、顾颉刚、张申府等名列在一位联大学生所评的不会讲课老师的名单中。
朱自清在“五四运动”时期就已经加入“平民讲演团”,听起来从教经验丰富,但他上课时仍不免紧张,得时时用手帕擦汗,一旦说错话直接上脸不知所措。他上课时不大敢讲自己的观点,总是引述别人的话和观点来给学生讲课。因此,选他课的人极少,他常常为此而焦虑。书中提到,最差的时候,只有研究生王瑶一个人来上课,但如果今天王瑶没来,那这课就没法上了。
闻一多则与朱自清相反,他年轻时口才并不佳,因为演讲不好而降等级,这被他认为是奇耻大辱。他为此一遍一遍苦练演讲,自信的他最终练就了一副好口才。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闻一多是激情的,是自信的,是具有煽动性的,这大多源自于对他演讲时的印象。
常人来说,性格如此相反的人,必然有相吸引的部分,也必然有相互排斥的部分。内心敏感多虑的朱自清对此则记录更多。书中举了一个事例,闻一多的孩子没告诉朱自清就从他的书桌上拿走了四本书。朱自清将这一举动看作闻家对自己的蔑视,对此他思来想去,忍了又忍,没有和别人说,并且怀疑闻家孩子并没有归还之意。而后,闻家孩子只还来三本书,那本没还回来的杰克·伦敦的书让朱自清觉得一定是弄丢了,并且最让朱自清恼怒的是,闻家孩子是趁朱自清不在的时候来还书的,并且对丢书一事一句都不提。这些事还有很多,但却从未影响到朱自清对于闻一多的佩服,在闻一多死后,朱自清也是尽其所能帮助闻一多家属渡过难关。作者在书中以李白与杜甫类比闻一多与朱自清的关系,确有些相似。
细节中的趣味
有些历史故事,与历史主线无关,但又隐隐地与历史人物有着各种关系。就像《世说新语》般,多是些人物趣闻。《说史记》中有一例人物趣闻,颇值得玩味。
北大学生傅斯年,有一天在北大附近散步,从北河沿走回沙滩,一辆车从他身边飞驰而去,溅了他一裤子泥点子。暴脾气的傅斯年,怒火中烧,回到宿舍就嚷嚷着“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”,说着说着开始和同学讨论关于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的问题,他把这些思考写成的札记发表在北大刊物《新潮》中,被学生们广为传看。
几个月后,“五四运动”爆发了,傅斯年任总指挥,之后的两三月中从不堵车的北京城,时常陷入因游行、演讲和警察抓捕导致的堵车中。清华的学生离城远,没能参加五四当天的运动,而是很快地参加到之后的北京高校罢课中。
6月的一天,游行的队伍到了西单,与一辆汽车狭路相逢,汽车的司机态度很差按喇叭要求学生让路。这个举动惹怒了清华学生们,人们想起了傅斯年发表在《新潮》里的那篇文章,大家将那辆车掀翻在路旁的沟里。这只是游行中的一个小插曲,但是有一位清华学生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,他开始对自己参加运动的意义产生了怀疑。回校后,他退出了运动,这个人就是散文家梁实秋。这虽说只是个小故事,但人们却能看到事件中各种人物的思考,以及他们呈现给世人的个性特点。
在故事中,人们能看到傅斯年的性格,也能看到那个时代的论事风气,更能看到对于历史大事件人们不同的理解。傅斯年直到去世仍旧是一副火爆脾气,而梁实秋则被冰心称作“像花一样的男人”,各自在中国文学、史学界中留下了一笔。
作者在书中用最合适的表达, 讲述了这些“不太重要”的历史细节。以文学赋予了历史更多的细节,尤其是在可读性上,文笔的舒展抵消了史料的干涩,让无趣的不枯燥,有趣的更幽默,让历史褪去了严肃、厚重,多了一份鲜明和生动,当后来人重新发现这些暗线时,或许能对那些印象中的历史人物或者事件有着更深的理解。